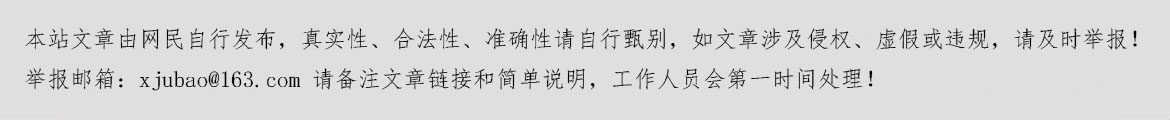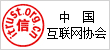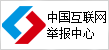揭开神秘面纱 让青少年了解性知识
2022-01-28 21:37:02
志愿者黄莉莉
“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,特郁闷,总有想哭的感觉”
一位同事告诉我,她认识一个人,“把宣传生殖健康当做业余爱好”。换句话说,这是一个罕见的性教育志愿者。
这个人就是黄莉莉。我和她聊了几次后,她所说的那些让她自己“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”的事,听得我也直觉得匪夷所思。
黄莉莉的“业余爱好”就是下班后,去一些朋友的单位义务讲座。她自己制作的电脑幻灯片,内容相当丰富,从最基本的男女生殖系统常识,从受孕到分娩胎儿的发育过程,到如何避孕,如何防治性病,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,国外关于性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,等等。她说,会根据每次的听众,相应做一些调整。
第一次做这样的讲座,是给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工程技术人员,内容涉及安全性行为,避孕,怀孕前的准备。
“有20来人,惟一一次男的比女的多。”回想起来,黄莉莉觉得那次讲座不太成功,因为“经验不足,语速太快,图片也没有现在多。”但让她很感动的,讲座开始前她声明,屋里不可以吸烟,要吸烟的到外面去。“我当时也担心会出来进去的,但过程中一个出去的都没有。”在座有3个女孩子,黄莉莉说,“她们的眼神让我感到,一定有什么是她们以前不知道或者没有想过的。”
“因为是工地,墙上都挂着安全帽,我就说安全套就像你们的安全帽,他们听了都笑。”“对着一群大小伙子你没觉得不好意思吗?”我问。“没有。”她回答得很干脆,“以知识传播性,没有什么不好意思。说起来,他们比我不好意思。”
这个爱好进行起来也不那么顺利。一个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想请她去,黄莉莉把自己的电脑幻灯片快递过去,不想单位里一位工会干部看了后说,图片太多,太露骨了。讲座也就黄了。
除了讲座,黄莉莉还在北京一家妇产医院做一项调查,对象是22岁以下,未婚,住院做终止妊娠手术的年轻女孩。住院做手术的原因都是因为孩子大了,不能在门诊做人工流产,只能做引产手术。
黄莉莉说:“我不知道这个调查有没有意义,我自己想一定是有意义的,因为我问到许多第一手的材料,好多听得我一身起鸡皮疙瘩。”
到目前接触过的近20名对象中,年龄最小的15岁,职业从无业、大中学学生、幼儿园和中学老师,以及服务人员都有。
“刚开始做这个调查时,特郁闷,总有想哭的感觉。”黄莉莉说。
不止一个姑娘不知道停经有可能意味着怀孕,好几个都把妊娠反应当做是胃肠胀气,去看中医吃汤药调经,还有的肚子大了以为是自己发胖,吃减肥药“减肥”。
“怎么会这样呢?怎么可能无知到这种程度?就算学校和家里不教,现在有那么多渠道了解相关的知识,网络、书、杂志,哪儿都可以看到啊。”我几乎是喊着说的。
“可就是这样啊!”黄莉莉说,也有的了解一些避孕知识,可就没想到要用在自己身上。有的认为怀孕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,怎么就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有的误以为医院不给未婚女性做人流,还有的因为没钱,不敢和父母说,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件事,也不知道拖下去后果严重,不知道生孩子要住院,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手术,要做很多检查。
“看那些孩子的经历和遭遇,可能就差一个人,一句话,只要有那么点知识,知道闭经可能就是怀孕,早一点去查,就不至于到24周去做引产,不会有那么多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。”
黄莉莉不是现在才有这种感觉的。
“我做了7年助产士,看得太多了。”1990年,卫校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北京一家医院做助产士。她很喜欢这个工作,因为在医院里“只有这里是和生命打交道的”。她自己有一个小本子,上面印着每一个她亲手接生的孩子的脚印。
有一天,她突然看到有人在楼道里哭。
“因为太奇怪了。”黄莉莉说,“一般产房外面的人都特别高兴。有着急的,没有那么伤心的,那个人哭的样子我至今都记得特别清楚。后来我就过去问,那是一个母亲,她流着眼泪和我说,女儿17岁,是美校的学生,在里面做引产手术。那个时候,未婚先孕的人还不像现在这么多。”
“因为这个职业,总有人来求你帮忙。第一个找我帮忙的是一个18岁的女孩,在手术室里她一直不说话,低着头,特别自卑。带着来的人会说,看你,给阿姨添多大的麻烦。实际上我当时也比她大不了多少。”
“说起这个我总是特别容易激动,因为我亲眼面对的太多了。”说着,她气哼哼地拿出一个笔记本,里面夹着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“无痛人流”的小广告。“这种东西太不负责任了,没有痛苦,不影响工作,不影响以后生育,怎么可能?你让他签个保证书看他敢不敢?”
“只要一个晚上能制止一个人流,就值得!”
每次讲座结束时,黄莉莉都要说的一句话是:如果大家喜欢,请帮我推广,邀请你们的朋友也来。采访中,有一天她高兴地说,听她讲座的人已经超过100个了。
“你看,我现在讲了100个人了,我就可能对这100人有一点影响,他们还可以再影响他们的朋友。”
黄莉莉说:“在医院,一个人工流产的费用1000多元,一个中期引产最多能到6000多元。稍微大一点的医院,一个月都能做几百起,干嘛给医院创收啊,所以,我办讲座,只要一个晚上能制止一个人流,就值得。”
“其实我挺强调自娱自乐的,业余爱好嘛。”她说,在这个过程中,更多是给自己带来很多快乐。你讲的东西人家愿意听,那是对你的一种鼓励和肯定。要搜集了解各种信息,讲得多了,自己的思路更清晰,表达能力也在提高,也是丰富自己。
她在产院做调查,也是希望能搜集足够的资料,做一些研究,如果可能,在妇产医院做一个项目,专门针对青春期少女,给她们讲一些基本的生育和避孕的知识。黄莉莉说,可惜北京没有类似重庆未婚少女紧急避孕中心那样的机构,“否则一定要调过去。”她认为,这类机构不应该定位在怀孕了怎么处理,而应该定位在宣传如何避免婚前性行为和如何避孕,让志愿人员出去讲。中学、职高、宾馆饭店,年轻人多的地方,还有进城务工的人。
“有需要的人太多了。”甚至,一位医院里原来的同事,还来邀请黄莉莉去给他们科室的护士做讲座。
“护士不是专业人士吗?”我觉得挺奇怪。
“护士也是隔行如隔山。”黄莉莉说,她认识的一个人,是内科护士,被诊断为宫外孕,医院让她住院,她自己偷跑回家。“晚上给我打了个电话,说我宫外孕了怎么办?我问她在哪儿,她说在家,给我吓得够呛。她一点也不知道宫外孕随时会大出血,有生命危险。”
生殖健康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,老师和家长也应该担负起相应的责任。
老师的态度非常重要。黄莉莉说,有次她到一所小学给女生讲月经,老师在旁边写板书。“我的题目是:每月一次奇迹,我们的朋友。老师自己嘀咕,多烦呀。老师这个态度,流露给学生的,肯定也是月经是件很烦的事。”
电视里播放卫生巾广告,7岁的儿子问爸爸,“那个结实又不漏的东西是干什么的?”
爸爸有点张口结舌,情急之下说:“补锅用的。”
儿子又问:“那妈妈每月都买补锅的东西干什么?”
黄莉莉说这是她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。“其实,如果父亲能利用这个机会,告诉儿子一些基本的生理知识,告诉儿子妈妈每个月会有几天特殊的日子,可能会身体不舒服,情绪不好,让他理解妈妈。如果这个孩子从小能理解妈妈,长大了就能理解其他女性,结了婚才会是好丈夫。”
“我也经常问我的朋友,你们说我是不是有毛病啊?一个女的,疯疯癫癫到处讲这些事。”黄莉莉说幸亏丈夫非常支持她,单位里有同事要结婚了,丈夫会和人家说“先来我家做培训。”
黄莉莉现在任职一个做健康教育的机构。两年前,她和在某部委工作的丈夫去美国生活了两年,回国时,原本可以有很多选择,但她最想的,是去中学里做一名健康教育老师。
可惜,她当时给很多学校发的自荐信都基本没有回音,最多说,我们不需要,有校医兼任。
不能专职就先当业余爱好来做,黄莉莉很有信心,“我肯定能做成,只是早晚的问题。
我有运气,想什么都能做成。真的不行,就等我退休了自己办一个生殖健康小屋,不就是当业余爱好做嘛。”